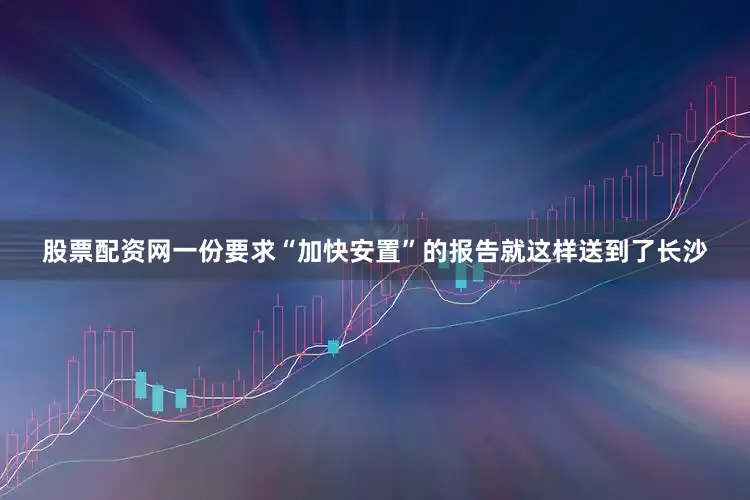
1974年的一个冬夜,十二月十六日,毛主席在长沙的客厅里问:“你看这些人该怎么安排?”他拿起那份名单,声音有些沙哑。周恩来接过名单,沉思片刻,还没来得及说话,毛主席又说:“都放了吧,办个欢送会,好好吃一顿,每人给一百块钱。”几句话,几年来的筹划终于有了最终的决定。
话音刚落,周恩来就立刻通知公安部,要求在三天之内了解所有未获特赦人员的身体、家庭和思想情况。华国锋紧接着把电话重重放在桌上说:“主席要大刀阔斧,我们就得抓紧时间。”与1959年第一批仅33人的初步尝试相比,这次的目标是确保一个不落。

从1949年开始,俘虏营里关了很多国民党的军官。那时候,台湾还没被解放,战争的威胁一直存在。对于这些俘虏,是判刑还是释放,是处决还是宽恕,中央政府选择了第三条路——先进行改造,再观察情况。刘亚楼还开玩笑说:“让他们先种几年菜吧。”谁也没想到,这个“种菜计划”竟然持续了整整十年。
1956年初,东风渐起,和平解放台湾的议题被提上了桌面。处理战犯的速度也随之加快。公安部将病残战犯的名单上报,希望能先释放一些。毛主席批得干脆:“表现好的战犯也要考虑。”周恩来则稳住阵脚,提议先挑选十来个看看效果,别一下子全部释放,以免引起社会情绪的波动。于是,1959年国庆前夕,首批特赦名单公布。
那年冬天,北京西花厅里灯火通明,黄埔军校的老同学杜聿明、王耀武等十位将军整齐地站成一排。周恩来拍了拍杜聿明的肩膀,语气就像当年在课堂上一样平和:“重新来过吧,路还长着呢。”杜聿明低头道歉:“学生愧对先生。”这句话让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。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温暖,后来释放了更多的将军。

1966年左右,国家形势变化多端,特赦的人越来越少,但政策没变:“不杀一个,分批释放”。周恩来经常提醒公安部要照顾年纪大、身体不好的犯人,“别让老人们在监狱里去世”。然而,实际释放的人数并没有增加,因为很多人是病死在监狱里的。1974年,一份要求“加快安置”的报告就这样送到了长沙。
主席指示的“欢送会”可不是做做表面文章。抚顺、西安、济南和北京四地的293位老人,都换上了崭新的蓝色便装,手里拿着背包、粮票以及一张新印的一百元。押送的工作人员私下里感叹:“几十年来,第一次见到他们这么有精神。”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时,车厢里竟然自发地响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虽然音调不太准确,但没有人阻止。
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里,六十张桌子依次排开,叶剑英、华国锋与被特赦的人们坐在一起。老将军李子亮提到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在香港和美国,话音刚落,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就记了下来。三天后,李子亮拿到了去香港的手续;一周后,他终于在旧金山见到了自己的儿子。沈策举起酒杯,眼眶湿润地说:“能让我的女儿来大陆看看吗?”负责联络的干部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可以!”

酒喝了几轮后,公安局请来了摄影师给每桌拍照,还特地多洗了一张给我留作纪念。几十年前,他们被拍照是因为被视为“战犯”;今天,镜头捕捉的却是普通人的笑脸。有人低声说道:“这辈子兜了个大圈子,又回到了原点。”
吃完饭后,并不意味着“各回各家”。周恩来把文化组的一张名单递了过去,点名让杜聿明、杨伯涛等人写回忆录,“亲口写,更有说服力,可以给后人做教材”。有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只会拉兵打仗,不会写文章,周恩来笑着摆手:“实话实说就是文章。”
农村的工作安排也是有讲究的。愿意到乡下工作的,每个月会有二十元的补贴;身体不太好的,可以去北京的一些老干部医院疗养。对于像卫立煌这样资历深厚且愿意出力的老同志,他们被邀请到了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,在档案堆里忙碌得很开心。即使七十多岁了,这些老同志还经常坐公交去上班,就像那些被返聘的退休老工人一样。

他们获得特赦后,并没有被置之不理。通过电话、广播和座谈会等多种方式,人们积极联络。一句“你们与台湾的老同事联系最方便,写信比我们登报更亲切”成了联络工作的口号。实践表明,这种方法很有效:几年间,许多两岸分离的家庭因此重新建立了联系。
有人会问,对过去的对手提供食物、金钱和工作机会,这样做值得吗?答案可能就隐藏在那些长长的名字背后。当社会充满坚定的信心时,宽容便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。1975年春天,北京城外的海棠花开得正艳。那一车穿着蓝色制服的人在晨光中下车,没有人再称呼他们为“战犯”。他们只是过了半百的普通人,准备开始他们余下的生活。
出彩速配-炒股入门与技巧-正规杠杆平台-股票配资中心网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